


《秋天的孩子》____

安穩待在印度的大學裡,任何人可以就這麼讀西印度群島的文本:把它當作一整個「新英文」文學創作連續體的一支。但是身處於加勒比海群島或非洲當地工作的印度研究者卻可能會被要求,要對於他或她與這些住在當地的印度裔住民的結盟關係講清楚,並且要說明白他或她從事比較研究的動機。
[這場公聽會]是一個開始,開始給那些無法發聲的人一個發言的機會,開始給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一個被放到中心的機會,開始給那些沒有力量的人一個賦予自己力量的機會。
在我完成寫作那個神話般的中國,那個我們在西方所虛構的神話中國,我去了中國。那個現實的中國就大概是我所想像的那個樣子…我們就是尚未可以脫掉尋權力求滿足的緊箍咒。一方面,湯亭亭到中國只是來印證自己的華美經驗想像,而不是以在地華人之眼來看中國;反方面,我們以華文中心位置來定位湯亭亭的華僑經驗,而無法站在她的在地掙扎去體會她的華美經驗。這兩方面問題全都再次顯示了我們仍然各自深陷在各自的三角關係裡,我們仍然沒有意識到我們對於絕對權力的默認,仍然沒有意識到絕對權力在我們身上的效應:如同湯亭亭一樣沒有意識到她自己的美國中心,我們也同樣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的中國正統中心。如果我們都無法辨識出絕對權力、無法面對自己赤裸裸的慾望,我們又該怎麼開始去面對這權力慾望呢?

…………藉由定位出這個國語政策的告密者角色/位階,我們在「國民義務教育」的課堂一代又一代地參與、操演而習得這告密者的個體心理學,及其情感結構。一方面,我們在其中經由「被出賣、因而受處罰」的經驗,共同地參與本省人第一代「被外省人騙」的情緒;另一方面,我們「出賣自己的社群」與「鞏固既有高階」,成為外省人、佔據高階而有機會得到滿足,不斷確立「我們是高於他們的」這樣的共同的語言經驗,一再維繫著外省人語言位階的優勢,再次認同執行國語政策的教師所代表的絕對權力中心──文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現代性階序邏輯。所以本省人/外省人的情緒結構才可以因此在不同世代之間垂直的「傳承」。
所以,面對著本省人粗糙的(crude) 「外省仔攏卡沒情」的描述,面對著外省人以「好台」、「台客」的形容詞來加強「本省人沒文化」的譏諷,本文沒有能力也並不以政治正確的觀點視之,而是將對於文明/殖民主義的見解,慨歎地以社會正義原理處理。
當本省人下一代開始以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非人」來思考的時候,他就僭越了不可跨越的殖民主義位階,這個僭越不再屬於私領域,而是一個公領域的事件;因為他應該是被殖民者、女人、黑人、小孩、外物、「非人」,因為本省人就是外省人的他者。
這樣的和解不意味著強制本省人與外省人要「分享共有」相互的苦痛記憶,反而是要看到彼此的悲情歷史的差異,及兩者的不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才可能相互的容忍。筆者如同陳光興一樣,都不樂觀以待。不過,這是因為本文對於大和解的期許是不同的:
西化的海外華人被迫要接受卑下的位置,甚至是對於自己的「不純正」而羞愧與不足的位置。在這個情況下,海外華人處於一個毫無勝算的處境:她不是「too Chinese」就是「not Chinese enough」。
放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殖民帝國主義的現代史來看,這群外省人是外來者/殖民者(settlers),暫居者{migrants),移民(immigrants),難民(refugees),或是現在流行的學術名詞,離散者(diaspora)?我們不只要問這些新潮名詞是否合用,更要問中文到底有沒有「不回家」的概念。
所謂的[海外華人]其實沒有共通的語言與風俗習慣可以在學理上成為獨立的範疇,而是相對於[在家的(at home) 華人]的範疇才有意義….海外華人的歧異,代換本省人的身分,不僅「語言不同,與中國大陸的連帶關係更是深淺有異」。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歧異聯繫著身分認同上所展現的世代差異:湯亭亭的父母親作為身不由己的華僑第一代,朝思暮想要回家的情緒,她完全無法體會,極欲擺脫,甚至是反對的。對湯亭亭來說,她除了從小長大的這個「鬼」地方的家,她無法在中國、香港、台灣或任何其他地方感受到「家」。她如同所謂的本省人,除了這裡這個家,她無家可歸;而她的父母親那一代則如同戰後來台的外省人,顛沛流離是人在江湖,滯留異鄉是身不由己,但是,終究都要回家的。這差異的鴻溝,這不同世代情感結構的「傳承」,如同本文的基本出發點,必然不只是眼淚的參與,而必須藉由下一代親身體驗的經驗基礎才得以親身體驗而得以「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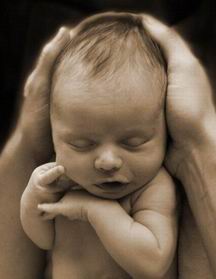
……這個因單一中國文化標準而形成的位階,以外省人的立場而言,就是你們本省人來學習我們的國語;終極的說,這是一個外省人的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在其中外省人是世界的中心,完全的自戀,而本省人則作為小孩、作為「非人」、作為「外物(object)」。弗洛伊德對於社會正義所開的最大的玩笑在此展現作用,這一把雙面刃有更大的危險:既然本省人必須禁制自己放棄日語去學國語,為什麼外省人就沒有這個問題?這可不只是權力位階高下,而更重要的是「不公平」。也就是因為不公平、不符社會正義,所以原本由於戰後國民黨政策的籍貫劃分所造成的本省/外省之別,就在這一把社會正義的利刃下截然二分。省籍問題之所以會是禁忌,就是因為這其中的不公平是不堪提起與質疑的。
相對的,比對前述台灣人﹝本省第一代﹞的群眾心理學,「多桑」這類「殖民地體制下小老百姓對於現代性的渴望」,這種「向上提昇」的慾望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並非本省人可以在「外省人vs.本省人」的架構中因種族或膚色無辨而僭越(pass)成為外省人,而是本省人已經把那個絕對的度量尺代換為「中國文化標準」,本省/外省關係因而被代換為「中國文化標準/外省人/本省人」的三角關係;這也就是說,本省人自日語習得的那個文化認同的彈性,事實上它的效果正是對於外省人自戀中心的反動。但是,為什麼外省人擁有中國文化而我們本省人沒有?反身自省的結果是,只要本省人可以像外省人一樣掌握國語,我們就可以像他們一般分得中國文化的一杯羹(equal share)。
在主觀的集體情緒結構上,兩條軸線平行發展,沒有交集,雖然在客觀的歷史結構狀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活在兩條軸線的交錯重疊中提供了關於殖民主義的不同見解。這是以語言的權力政治去捕捉這些俗世經驗裡的大術語,以及其成為禁忌的理由;並且,社會正義原理在這些語言經驗裡,清楚地定位出不同殖民位階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第一代各以個體心理學和群眾心理學去面對對方。有許多詞彙與現象仍然一再重複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全都活在這些歷史的現在式裡,面對著血淋淋的刻板印象,醜惡的嘴臉,空泛的美麗幻夢。
它的效果…是去殲滅一個民族的信仰,而這個信仰是對於他們的名字、對於他們的語言、對於他們的環境、對於他們歷史掙扎的遺產、對於他們的延續、對於他們的能力,以及終極地對於他們自己。這使得他們看待自己的過去猶如看待一個毫無成就的荒原,並且這使得他們慾想著要將自己遠離這一個荒原。這使得他們慾想著要認同於那個與他們自己最遙遙無關的[文明];例如,認同於其他民族的語言,而不是他們自己的。古基談語言,是以本土主義的方式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母語的「自然」對抗國語政策的「人為扭曲」。雖然肯亞在二次大戰前已經是英國殖民地,嚴厲的國語(英語)政策卻是自1952年獨立之後才開始:「在肯亞,英語變成不只是一個語言:它是那個[唯一的]語言,而所有其他語言都必須卑躬屈膝地尊英語為尚/上」。
帝國主義,由美國所領導,向他們─地表上掙扎求生存的各民族,以及所有尋求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人─亮出了最後通牒:接受豪取橫奪,或者死亡。但是,冷戰鬆動之際對於「美帝」的撻閥之聲中,我們仍然無法滿足於這一個結論,因為冷戰時期肯亞和台灣進行著帝國/殖民主義的深化,不只意味著目前「去殖民」「去冷戰」的迫切,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帝國/殖民主義母國為中心本位的個體心理學一再深化,而其深化必然意味著肯亞和台灣兩地在地一再強化告密者的個體心理學。當然,我們必須個別地面對在地的經驗,而告密者個體心理學的巧合對我們透漏著:冷戰結構,意味的,不只是美/蘇左右意識型態的爭鬥,而是再次強化與鞏固既有文明/殖民主義的結構─被殖民者繼續作為被殖民者─,以確保以美國為首的帝國/殖民主義母國的最大利益。
所有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最底層的情緒結構…在全球各地的殖民地…被[在地的]政治精英轉化挪用成奪權的動員資本…或是以冷戰中的反共為藉口來打壓異己,最後以內戰與族群鬥爭的表現形式,持續了殖民主義的基本邏輯。法農最後的呼籲,古基對帝國主義的控訴,以及我們沉重的心情,一再見證著重蹈覆轍的傷痕。到底是我們對於殖民主義的驅魔不夠徹底?還是因為殖民主義的邪惡正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



 A)這音樂網站,1出手就不得了啦,首先是這參件前所未見的重頭文章~
A)這音樂網站,1出手就不得了啦,首先是這參件前所未見的重頭文章~

 第3部份為
第3部份為
 重頭戲在這里::
重頭戲在這里::





《思戀(蓮)歌》詳細資料
種 類 /山歌小調
作品主要名稱/ 思戀歌
作品其他題名/又寫成《思連歌》,亦有人誤寫為《思蓮歌》
封面題名/ 山歌大會串
全集題名/ 客家民謠
錄製者/
錄製時間/
錄製地點/ 台北市(佳聲錄音室或和鳴錄音室)
ISRC/
國際標準錄音/影資料代碼
作 曲 者/ 民謠
作 詞 者/ 民謠
表 演 者/ 葉香蘭、邱玉春
製 作 人/
捐 獻 者/
內容主題/
使用場合與功能
風格/時期/
曲 調/ 傳統音樂--(小調)《思戀歌》
曲 式/
使用樂器/ 胡琴(椰胡、喇叭弦、高胡、大廣弦)、鑼鼓(鼓、敲仔、拍板、大鑼)
使用語文/
得獎紀錄/
得獎時間/
創作時間/
創作地點/
資料來源 唱片提供者/月球唱片廠
解說撰文者/徐于芳
備 註/ 初版唱片編號/8140(第四十集)/
改版卡帶編號:12
[ 歌 詞 ]
正月(來)思(啊)戀真思戀,打扮幼三妹,
打扮幼三妹,打扮三妹、三妹過新年(喏-吶唉喲喲得喲)。
打扮(來)三(啊)妹、三妹來飲酒,杯杯(啊又)盞盞,
杯杯(啊又)盞盞,杯杯盞盞、盞盞過新年(喏-吶唉喲喲得喲)。
二月(來)思(啊)戀(思戀)真思戀,打扮幼三妹,
打扮幼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落花園(喏-吶唉喲喲得喲)。
打扮(來)三(啊)妹、三妹花園溜,手攀(啊有)花枝,
手攀(啊有)花枝,手攀花枝、花枝笑連連(喏-吶唉喲喲得喲)。
三月(來)思(啊)戀(思戀)真思戀,打扮幼三妹,
打扮幼三妹,打扮三妹、三妹來蒔田(喏-吶唉喲喲得喲)。
阿哥(來)蒔(啊)田、蒔田妹蒔糯,兩人(啊)共一蒔,
兩人(啊)共一蒔,兩人共蒔、共蒔一坵田(喏-吶唉喲喲得喲)。
四月(來)思(啊)戀(思戀)真思戀,打扮幼三妹,
打扮幼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落茶園(喏-吶唉喲喲得喲)。
嫩茶(來)摘(啊)來、郎呀郎去賣,老茶(啊)摘來,
老茶(啊)摘來,老茶摘來、摘來做工錢(喏-吶唉喲喲得喲)。
五月(來)思(啊)戀(思戀)真思戀,打扮幼三妹,
打扮幼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落茶園(喏-吶唉喲喲得喲)。
蓮葉雙雙水(啊)面上、端陽節氣到,端陽節到,
端陽節到,節到又一年 (喏-吶唉喲喲得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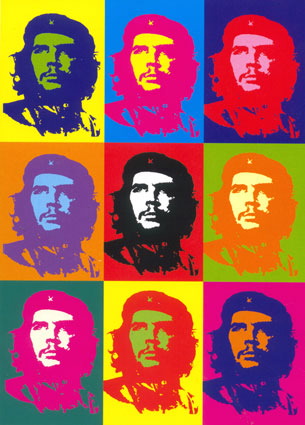















我們 當下任務宛如追憶歌仔戲老唱片的似水年華, 其實我們是在緬懷和探究上世紀專注於「聆聽」的那個時代精神/文化—— 電視這個機器/媒體/怪獸尚未吸吞/侵噬民眾之眼球與腦洞的50、60年代, 咱們的青壯年阿嬤使著猶未衰老的秀麗耳朵伴隨一個 「仍未被恰當定義」的歌仔戲盛世安身立...
